|
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https://www.td010.com 被联名驱逐的7岁女孩 在贵阳「顶流」小学,一个7岁的小女孩被37名同班同学的家长联合驱逐了两次。 最终被迫转学。 无法想象,这场驱逐风波的导火索,竟然是没完成的家庭作业。 女孩的名字叫妞妞,身患哮喘病。 去年11月3日,班主任翟老师要求妞妞在办公室补写落下的家庭作业。 放学回家后,妞妞突发哮喘。 妞妞的妈妈认为课业负担是发病的诱因,给老师打电话抱怨: 「作业太多,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没法承担。」 翟老师的回复很简单: 「你们受不了就自己转走。别再来读我们这个学校,读我这个班。」 第二天,该班级的家委会避开妞妞的父母单独建群。 随后,家委会的新群里赫然出现了一封「请愿信」。 请愿信的内容很简单——希望学校劝谏妞妞退学。 请愿信列出了妞妞妈妈的三大罪状: 一、不参加班级集体活动,影响班级荣誉; 二、反对孩子加强课后练习,反对老师批评孩子; 三、微信、电话骚扰历任和现任班主任。 家委会的成员呼吁众家长在联名信上签字。 为了治疗哮喘,妞妞妈妈每天下午都会带妞妞去医院,其他家长认为: 下午长期不上课,是在蔑视学校规章制度。 第一次的联名驱逐并未成功。 今年3月15日,妞妞妈妈要求进入校园接孩子,被校方拒绝。 妞妞妈妈担心孩子在学校受欺负,强行翻越学校伸缩门,矛盾进一步激化。 家委会再写联名信。 这次,除了妞妞妈妈,全班只有一位家长拒绝签名。 两封联名信被一起交给校方后,妞妞被迫休学。 一个7岁的孩子,在这场「教育之战」中,成了牺牲品。 「内卷」和「鸡娃」是一场全社会的无声悲哀。 悲哀下,是无能为力的父母。 赶走那个说不的人! 妞妞的妈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: 不从众,是妞妞被驱逐的真正原因。 班里的大多数家长认为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并不多。 孩子写三四个小时,是因为他们注意力不集中,太磨蹭。 翟老师说「成绩不到95就不算优秀」,家长们非常认可。 为了让孩子拿到更高分,甚至在家长群里公然授权老师对孩子使用暴力。 可妞妞妈妈认为这会让孩子觉得: 唯有分数能带来荣誉感,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。 一个重视应试教育的班主任,一个推崇快乐教育的妞妞妈妈,必然会因教育理念的不同发生冲突: 她反对学校只让踢球优秀的孩子参加比赛,让其他孩子穿着单薄的球衣在寒风中发抖; 她反对家委会的成员随意出入校园,其他家长只能校外等待; 她反对鸡娃,认为身体健康,快乐成长最重要...... 这些反对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,也打破了家长对高分教育的期待。 在知乎,《给妞妞妈妈的一封信》里,班里的其他家长对妞妞妈妈的印象很差。 家委会成员,也曾劝导她服从老师的安排。 如果妞妞妈妈的描述属实,那么家委会俨然是一个拥护老师权威,对老师唯命是从的机构。 老师根本不需要说话,家委会就是老师利益的代言人。 而妞妞妈,则是老师和家委会的眼中钉。 谁是这场风波中真正被驱逐的人? 不是7岁的妞妞,而是她的妈妈。 是一个想和老师平起平坐的家长。 是一个群体中的异类。 联名信时间后,妞妞的妈妈向各级部门提交举报信,举报翟老师: 教唆、指使家委会单独建群,孤立学生,同时收受礼物,违规超纲教学,违规排名…… 贵阳市教育局经调查发现: 翟老师存在教师节期间收受家委会礼品、公布成绩排名、考试前漏题、对家委会排除个别家长单独建群问题默许并参与等行为。 据此,教育局给予翟老师全区通报批评,撤销年级组长职务,取消「市级名班主任」称号,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。 谁知此举竟惹得众多家长非常不满。 住同小区的家委会家长,甚至在小区业主群里上演了另一出闹剧: “把指甲整尖一点,一起去家里送祝福” “快把门牌号码人肉出来” “往死里打,大不了赔钱” ...... 家委会的行为,实在是令人发指! 孙隆基在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中,对这类情况做了精辟的归纳: 中国人的倾向不欣赏一个人有“个性”,而是欣赏一个人“跟大家一样”。 为了获得大家认可,中国人要搞斗争,也必须说是为了“整体利益”。 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说成是为了保持团结,并尽量把自己对手的斗争说成是破坏团结的分裂行为。 集体,成了人们排除异己的武器。 此时再看家长联名信上,动辄提到「班级荣誉,学校规章」,是那样讽刺和丑陋。 事实上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有些家长表示自己并不认同家委会的做法。 但他们还是迫于压力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 这些违心签名的家长,不敢反抗家委会的淫威。 生怕自己的孩子因此成为下一个妞妞。 这正应了米歇尔·巴德利在《盲从与叛逆:从众、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》的第二章,赫然写下的那句话: 我们更加隐性和下意识地屈从于同伴压力和社会习俗的需要。 不屈服则意味着尴尬、冲突和困惑。 驱逐一个反对者,就能让所有潜在反对者闭嘴。 好一个杀鸡儆猴。 不敢快乐的中国人 被驱逐的事情上热搜后,妞妞妈妈的博士身份和她的快乐教育理念,被网友反复提起。 其中的高赞评论是这样说的: 两句话,说尽了广大家长的焦虑与无奈。 对一个家庭来说,孩子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,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意味着一场硬仗。 教育资源有限,要想拿到名校的文凭,需得分秒必争。 按照2019年中考录取的分数线,要上「四大名校」之首的深圳中学,每门课平均分要达到95分。 辅导机构牢牢抓住了家长的焦虑,打出了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标语: 「你来,我们培养你的孩子; 你不来,我们培养你孩子的对手。」 育儿变成了一场「军备竞赛」,好像输在起跑线,就输了人生。 根据2018 年发布的《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》显示: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94% 的一二线城市父母存在焦虑情绪。 其中,孩子在幼儿和小学阶段,家长们最焦虑。 于是,孩子上辅导班的年纪越来越小,父母鸡娃的手段也越来越极端。 在纪录片《你好,儿科医生》中,一个3岁的小男孩因为不喜欢上辅导班哭闹,被妈妈踢到下体出血,送医急救。 儿科医生们看到伤势后都大吃一惊,急忙安排手术。 但伤子的妈妈却一个劲儿地抱怨着: 「和别的父母比起来,我报的课后班算少的了。」 这位焦虑的母亲,难道不想孩子快乐成长吗? 不,她只是不敢让孩子快乐。 因为在家长的世界里,那些放纵孩子快乐成长的孩子,最终会害了孩子。 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报道中,一位三年级女孩的妈妈在老师办公室里陷入焦虑。 三年级的第一次数学课上,试卷里的题女儿一道也没有见过。 老师反复跟她强调: 「你知道这是三年级了吗? 你真的没给孩子报课外班吗?」 想在中国的高考体系里混下去,三年级是个坎儿。 一、二年级时,教育部明令禁止考试。但到了三年级,学习成果就有了分数的考量。 如果这时候家长还保持佛系,就会被视为放弃国内体系的竞争路线。 这位一向讲究快乐育儿的母亲,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焦虑。 身边的家长也纷纷劝她尽早给孩子报班,「再不学就晚了」。 每一个「合格」的家长都是一个长线规划师,他们拼尽全力为孩子规划着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人生坦途。 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终极目的,那就是:上个好大学,找份好工作。 为了摆脱社会上的学历歧视,为了让孩子免于面朝黄土背朝天。 教育,俨然成了父母卷孩子,最好的捷径。 可如此一来,却让全社会陷入了恶性竞争。 80后为了读一所好大学,大多从高中开始挑灯夜读,奋战三年; 90后为了读一所好大学,最多也就是初二开始补习高一的知识,以保证顺利通过不足50%的初升高独木桥; 00后的起跑线就更早了,刚上小学就开始报名各种夏令营,参加奥数、英语补习班,培养特长; 10后就更不用说,幼儿园阶段就人均熟练掌握两门语言,体育老师都是清华数学系毕业…… 在学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,这届孩子想达到和父母一样的高度,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。 这看似努力的良性竞争,不过是一场零和博弈罢了。 更糟糕的是,就算孩子真的样样出色,也未必能拥有想要的人生。 在《上岸: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》一书里,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反面案例: GPA 4.0,全美AP学者奖; 北美高中Quiz Bowl比赛冠军队主力; 学钢琴11年,作曲5年,获国家级钢琴比赛B组最高奖; 10岁时出版两本小说,当地电台主持人,上过当地报纸,累计300小时公益活动,跆拳道黑带…… 拼尽全力打造出如此完美的简历,但在申请全美排名前25的大学时,却无一通过。 最终,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: “也许我们应该反思,把孩子变成流水线上精心打造出来的完美‘产品’,到底有没有必要?” ✎✎✎ 为了减轻内卷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简称“双减”政策)。 双减政策规定:严禁超前培训,严禁占用休息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,严禁刊发校外培训广告。 但鸡娃的家长们并不买账。 他们迅速想出了各种应对之举: 不让补课可以,但孩子体育社团的体育老师,最好是清华数学系毕业,且擅长奥数教学。 好像孩子的童年,只有一件正事——那就是学习。 而在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之中,国际记者周轶君走访芬兰。 在当地的健康服务中心,她遇到了很多和小学生一起学画画的老人。 这些小孩和老人学画画的目的,仅仅是喜欢。 带队的小学老师拉妮的一句话,让我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震撼。 她说: “这些画不是用来彼此竞争的。所以他们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。” 这个世界,根本不缺「卷」出来的流水线做题家。 缺的是住在快乐星球的小小少年。 教育,不该只有一种面貌。 另辟蹊径,或许能看见更多美好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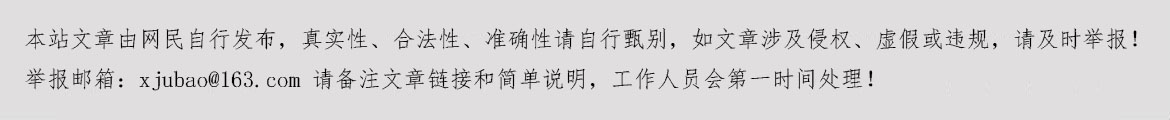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• 新闻资讯
• 活动频道
更多




